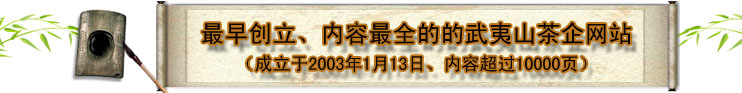|
根据客人的多少来决定茶事活动的繁简。三人以下,只生一炉火就可以了;如果有五六人,就应当用两个鼎炉。每一炉专用一个童子,调和烹煮和点茶。如果一人兼顾两炉以上,就恐怕会操作不当或者出现差错。
煮水的火,要数坚硬的木炭所烧的为最好。然而木炭的木性尚未消失殆尽,还有残留的烟气。烟气一旦进入水中,那么水就一定不能饮用了。因此要先把木炭烧红,使其烟焰冒尽,同时在火力最猛烈的时候开始烧水,这样水就容易沸腾。等到木炭烧红之后,再放上煮水器具,仍然要急急扇火,使水开得越快越好;不要停止扇火,一旦停手之后,宁可把水倒掉,再重新烹煮。
茶事活动不适宜接近的外部环境包括:阴暗的房屋、厨房、喧闹的市场、小孩啼哭、性格粗野的人、侍童和佣人相互起哄、酷热难耐的斋堂居舍。
明代罗廪《茶解》中说:茶的色泽以白为贵,茶色鲜白,味道甘甜鲜美,香气扑鼻,这样的茶可以称为精品。茶中的精品,冲泡得淡时固然呈白色,冲得浓时也会呈白色,刚刚沏好时呈白色,存放久了依然是白色。茶味甘甜,茶色鲜白,其香气自然芬芳四溢,色、香、味三者都具备了,那么精品茶叶的标准也就具备了。近来有好事之家,有人担心茶色过重,一壶开水只投放几片茶叶,不仅茶味不足,而且香气也十分淡薄,终究免不了要遭受水厄那样的讥讽。即使这样,特别关键的还是要精心选择烹茶用水。茶的香气,以如同兰花的香气为最好,如同蚕豆花的香气次之。
烹茶一定要用甘甜的山泉,其次是梅雨水。梅雨如同膏泽滋润大地,万物赖以生长,其味道独具甘甜的特色。梅雨季节过后,雨水就不可饮用了。梅雨水汲取之后要倒满一个大瓮进行贮存,其中要放上一块伏龙肝以便澄清水质。伏龙肝就是炉灶中心的干土,要趁热放进水中。
宋人李南金认为,煮水火候的把握应当以背二涉三即第二沸和第三沸之际为合适,这的确是鉴赏家的至理名言。而罗大经先生害怕水煮得过老,想在开水发出松涛涧水一般的声响之后,将水壶从火上移开,稍等一会儿沸腾停止,再来烹茶。这种说法也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殊不知开水煮老了之后,即使从火上移开,又怎么能够补救呢?
贮存泉水的陶瓮,必须放置阴凉的庭院中,用纱巾或者布帛覆盖,以便使其白天吸收阳光,夜间承接星光雨露之气,从而使泉水的灵气不致消散,泉水的神韵长久保存。假如在陶瓮上面压上木板或石头,或者用纸、箬叶密封,在太阳下面暴晒,这样里面封闭和凝滞泉水的灵气,外面则耗散泉水的神韵,那么泉水的精神就损坏了,泉水的味道也就败坏了。(此节不见于《茶解》而见于张源《茶录》)明代屠隆《考馀事》中说:如今茶叶的品类与陆羽《茶经》的记载大相径庭,而且烹制的方法,也与蔡襄、陆羽等人所说的方法完全不同了。
观察煮水沸腾的情况,开始的时候水面犹如鱼眼,微微有声响起,这就叫做一沸;水面边缘犹如涌泉、连珠,这就叫做二沸;水面犹如浪涛奔涌、水沫飞溅,这就叫做三沸。煮水的方法必须使用活火。如果用柴薪煎煮,火力刚刚上来,水和锅刚刚烧热,马上就倒水冲茶,水汽尚未消散,称作水太嫩;如果人过百岁,水过十沸,才开始冲泡,那么开水已经失去其本性,称作水过老。太嫩与过老,都不可用。
明代周履靖《夷门广牍》丛书所收徐献忠《水品》记载:苏州虎丘石泉水,唐朝刘伯刍品评为天下第三,陆羽(字鸿渐)品评为天下第五。因为石泉清洌深邃,都是地下积累的雨泽,是山中渗出的泉水。况且虎丘本为春秋时代吴王阖庐的墓道,当时修墓的石工都被关闭其中而死;而且虎丘寺中僧众住在上面,不可能没有污秽之物渗入地下。虽然名叫陆羽泉,却不是天然水脉。道家服食养生,禁止与尸气接近。
明代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记载:杭州西湖的水,汲取贮存于大缸之中,澄清六七天。如果遇到风雨天气就盖起来,天气晴朗就打开来,使其接受日月星辰之气。以此水来烹茶,甘甜醇厚,很有滋味,不逊于惠山泉水。这是因为西湖水由四周山谷溪流奔腾注入,蕴涵凝聚,并不仅仅是一水,这样摄取精华多,自然味道充足了。由此可知凡是湖泊巨浸的去处,都可以贮存其水加以澄清,水质绝对胜过浅水细流。阴井中的水,浑浊凝滞,味腥而且淡薄,不可用来烹试点茶。
古人好奇,在饮品中制作百花熟水即花茶,又制作五色饮品,以及冰蜜、糖药等,各种名目自不相同。我认为都不足以推崇。如果正好逢上好茶缺乏,用劈得很细的松枝开水冲泡,也可以饮用。
李日华《竹懒茶衡》中说:天下处处都有好茶,然而名茶胜地没有时间一一身临并品尝,姑且根据距离较近地方所产日常可以品尝的茶叶略加品评:苏州虎丘茶香气芬芳,而滋味淡薄,初入茶盏,菁英浮动,闻起来如同初析的兰花,品饮之后口感也相当爽快,但必须用惠山泉水冲泡,泉水的甘甜醇厚足以弥补茶叶的滋味淡薄。杭州西湖的龙井茶,味道极其醇厚,色泽如同淡淡的黄金,香气则沉寂而不易散发,品饮时间久了,就感到鲜嫩潮舌,必须借助杭州虎跑泉空寒冰冽的泉水来进行发挥,然后才感到滋味绵长,没有浑浊凝滞的遗憾。
李日华所撰松雨斋《运泉约》中说:我们这些嗜茶的同道,神情交合于竹林雪野,烹煮如松风涧水般的山泉好茶,暂时随俗饮食人间,终究要逍遥尘世之外。天下名山尚未游历,如何能够辞却尘海、超然物外呢?然而搜奇炼句,作为文章,灵感思绪容易枯竭;涤除积滞,清除昏蒙,只有坚持汲水煎茶,不废茗饮。朋友寄来佳茶三百片,高兴地拆开书信;一堆槐枝燃起的篝火上,山泉之水刚泛蟹眼,正可烹茶。陆羽的《茶经》,已经被奉为典型;张又新的《煎茶水记》,不能不加以议论。从前李德裕(封卫国公,世称李卫公)官至太尉,还颇为运送泉水劳心;杜甫晚年隐居在夔峡,惊叹山势险峻,胜地湿云。如今我们环处惠山之下,相距不过二百里之遥;如果从松陵(今江苏吴江)渡江,也不过三四天的行程。汲取新泉,捐弃旧水,就像运用辘轳一样转手;方便汲取,费用又省,就像运用桔槔一样快捷省力。凡是我们清雅之士,希望都能前来加盟!转运惠山泉水,每坛偿付船运人力费用白银三分,水坛的坛价及坛盖自备,不计在内。泉水运来,请报告各位朋友,让他们各自前来运走。每月的上旬收取费用,中旬运水。每月转运一次,以保持泉水的清新。请愿意加盟的朋友在左边写下名字,以便造册登记,连同所要坛数,如数交付银钱。
尊号 用水 坛 月 日付 松雨斋主人谨订
冒襄《茶汇钞》中说:烹茶的时候,首先要用上品的泉水洗涤烹茶用具,一定要新鲜洁净。其次要用热水洗涤茶叶,水如果过热,恐怕经过洗涤会损坏茶味。应当用竹箸夹着茶叶在洗茶的器具中反复洗涤游荡,祛除其中的尘土、黄叶、老梗等。洗过之后,用手拧干,放到洗茶的器具中盖好。过一会儿打开观察,色泽青翠,香气甘洌,这时候急忙取沸水冲泡,效果极佳。夏季要先备好水而后放茶叶,冬季则要先备好茶而后放水。
茶的色泽以白为贵,然而色白也并不难做到。如果能做到泉水清澈、茶瓶洁净、芽多叶少、水味甘测,随即烹茶随即品饮,其色泽就自然会鲜白,但是茶叶的真味蕴结而未能发挥出来,仅仅是为了一饱眼福罢了。如果取青绿色泽为贵,那么苏州天池茶、徽州松萝茶以及长兴的罗茶中的最下等茶,即使在冬季,其色泽也会如苔藓般青绿可爱,何足为奇?像我所收藏的真正的洞山老庙后上品茶,自谷雨后第五天,用开水冲洗荡涤,贮于壶中很久,其色泽依然鲜白如玉。到了冬季则色泽嫩绿,味道甘美,色泽稍淡,韵致清新,香气醇厚,也作婴儿肉的香味。其芳香浮荡,这是虎丘茶所不具备的。
明代周高起《洞山茶系》中说:罗茶品质优异,其功劳只是在于洗茶并控干。用沸腾的开水泼洗茶叶,随即捞起,用洗鬲(一种沥水的工具)敛出其中的水分,等到开水稍凉可以放进手指的程度,就放下洗鬲清洗排荡出沙土和浮沫;然后再捞出来,用手指控干,放到封闭的容器中等待冲泡。因为其他茶叶都要把握煮水的时机分别投茶烹点,只有罗茶经过清洗控干之后,芽叶软绵润泽,所以只须上投(即先注水后下茶叶)。
《天下名胜志》记载:宜兴县湖镇有一个于潜泉。泉穴宽约两尺左右,形状好像水井。其泉源到泉穴之间有伏流相通,味道非常甘冽。唐朝的时候这里制造贡茶,此泉水也随着贡茶一起进贡朝廷。
太湖洞庭西山缥缈峰西北,有一个水月寺。寺东进入小青坞,有一泓泉水清澈甘凉,一年四季不会干涸。宋人李弥大(字似矩,号无碍居士,晚年隐居苏州道隐园)将此泉命名为无碍泉。
安吉州(今浙江湖州安吉县)的泉水,以碧玉泉为第一,泉水清澈可以照见头发,清香可以用来烹茶。
明代徐献忠《水品》中说:泉水甘甜,如果称量试验一定会比较重。这是因为其源远流长的缘故。扬子江南零水,从岷江发流,奔腾数千里才到达镇江金山下的两个大石之间,澄清之后,品质优异,其性厚重,其味甘美。
陆羽的《茶经》,不仅选择品鉴泉水,还论述了煎茶用炭火或者木质坚硬的柴薪木。木炭如果曾经燃烧、沾染了油腻腥膻气味的,以及含有油脂的木柴、腐朽废弃的木器,都不可用。古人分辨用过的木器炊煮食物会有怪味的说法,应当说是有其用意的。
山脉深厚、山体雄大、山势盛丽的地方,一定会出上佳的泉水。
明代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中说:茶的自然本性必须借助水来发挥出来,八分的好茶,如果用十分的好水来烹点,那么茶的效果也就达到十分了。如果用八分的好水,烹试十分的好茶,那么茶的效果也只能达到八分罢了。
陈继儒《岩栖幽事》中说:黄庭坚《煎茶赋》写道:“汹汹乎,如涧松之发清吹;浩浩乎,如春空之行白云。”可以说是得到了煎茶的真谛。
陆绍珩《醉古堂剑扫》中说:扫叶煎茶乃是格调幽雅的事情,必须人品与茶品相得益彰。因此煎茶的方法往往流传于高人隐士、有烟霞泉石堆积胸中也就是向往隐逸生活的人们中间。
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记载:天下第四泉,在江西上饶县以北的茶山寺。唐代陆羽曾经寓居此地,就在这里的山上种植茶叶,汲取此泉水煎茶,品鉴其为天下第四泉。当地人尚书杨麒早年曾经在这里读书,于是取“茶山”二字为号。
我在北京三年,汲取德胜门外的泉水烹茶品饮,效果最好。
皇宫中御用的井水,也是北京西山的泉脉所灌注的,的确是天下第一等的泉品,这是茶圣陆羽《茶经》所没有记载的。
俗话说:“芒种逢壬便立霉。”霉(指农历入伏前的几天多雨潮湿)后接取雨水烹茶,极为芳香甘测,而且所接雨水还可以久藏。时节一到夏至就迥然不同了。我经过试验,的确如此。
居住家中,难得泉水,于是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取平常的水烧开,然后放入大磁缸中,放置庭院中,避开阳光照射。等到夜间天色皎洁,打开磁缸接受露水之气,如此共经过三个晚上,其水清澈见底。缸底堆积尘垢两三寸,这时赶快将水取出,用坛子盛起来,用来烹茶,与无锡惠山泉没有两样。
明代闻龙《它泉记》记载:我的家乡四明(今浙江宁波)四周都是山,到处都有泉水,可是都味淡而不甘美。只有所谓的它泉,其泉源出于四明山,从潺洞经过许多山涧到达它山埭(唐代鄞令王元伟筑),不下数百里,水的色泽蔚蓝,水中白沙白石,粼粼见底,水质清澈寒冽,甘甜绵滑,可以称为全郡第一。
明代焦《玉堂丛语》记载:明代翰林学士黄谏曾经写过《京师泉品》,认为城郊的泉水,以玉泉为第一;城中的泉水,以文华殿东大庖井水为第一。后来他被贬为判广州府事,著《广州水记》品评泉水,以鸡爬井为第一,更名为学士泉。
吴说:武夷山的泉水,出于南山的,都是洁净甘洌,但回味不长;出于北山的,泉味则迥然不同。这是因为两山形状虽然相同,山脉却不一样。我曾经携带着茶具去探访品尝山泉,共计三十九处,其中最差的泉水也没有硬冽的气质。
清代王士祯(新城人,世称王新城)《陇蜀馀闻》(载《池北偶谈》)记载:成都百花潭中有三块巨石,水从其中流过,汲取此水煎茶,比其他水更加清澈甘冽。
王士祯《居易录》记载:河南省济源县段少司空园,是唐代卢仝(号玉川子)煎茶的地方。园中有两处泉水,有人称为玉泉,距离盘谷不到十里;园门外有一条河,叫做漭水,发源于王屋山。查阅《河南通志》,玉泉在泷水上,卢仝曾经煎茶于此,现在通行的《水经注》没有记载。
王士祯《分甘馀话》记载:一水(即水,又名龙鱼川),是一个水名。郦道元《水经注·渭水》记载:“又东汇合一水,发源于吴山。”《地里志》记载:“吴山,就是古代的山,山下有一个石穴,泉水外溢,石穴中空,悬空的水流从一侧垂下来。”这就是一水的源头,在灵应峰之下,即所谓的“西镇灵湫”。我在丙子年(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祭告西镇的时候,经常在这里品茶,其水味与北京西山的玉泉极为相似。
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中说:唐朝刘伯刍品评天下泉水,以扬子江中泠水为第一,无锡惠山泉水、苏州虎丘寺石水次之。陆羽品水,则以庐山康王谷为第一,而以无锡惠山泉水次之。古往今来的轻信传闻的人们于是就认为这是不可更改的定论。其实二位先生所见到的,只不过是江南数百里之内的泉水,更远的地方例如峡州(今湖北宜昌)的虾蟆碚,只不过独此一例罢了。不知道长江以北地区比如我的家乡山东济南,挖地皆有泉水,其著名的就有所谓七十二泉。用来烹茶,品质都不在惠山泉水之下。
宋代李格非(字文叔),是我的同乡前辈,曾经著作《济南水记》,与其《洛阳名园记》并行传世。可惜《济南水记》已经散佚无法匡正刘、陆二位先生疏漏罢了。谢肇(字在杭)品评他平生所见到的泉水,济南趵突泉名列第一,其次有益都孝妇泉(在颜神镇)、青州范公泉,尚未见到章丘的百脉泉,以上这些都是我故乡的泉水,二位先生何曾见识更多。我曾经给王苹(字秋史,历城人,居圣水泉畔,即济南七十二泉之第二十四泉)的二十四泉草堂题词说:“翻怜陆鸿渐,跬步限江东。”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清代陆次云(字云士,钱塘人)《湖杂记》记载:龙井泉从螭龙口中流出来。水在池内,其气质恬然。如果游人注视很久,就会忽然间波澜涌起,如同将要下雨一样。
清代张鹏翮(字运青,麻城人)《奉使倭罗斯日记》记载:葱岭乾涧的旁边,有两个旧井,从井旁掘地七八尺深,就可以见到水,水味甘甜清凉,可以用来烹茶,命名为塞外第一泉。
明代陆应《广舆记》记载:永平滦州(今河北滦县)有扶苏泉,非常甘测。传说秦始皇长子扶苏曾在这里休息。
江宁摄山(今江苏南京市栖霞山)千佛岭下,石壁上雕刻着六个隶书大字:白乳泉试茶亭。
所谓钟山(今南京市蒋山)的八功德水,是指一清澈、二寒冷、三芳香、四柔和、五甘甜、六洁净、七不(久而变质发臭)、八蠲疴(社除疾病)。
丹阳(今属江苏)的**泉,唐朝刘伯刍评论此水为天下第四泉。
宁州(今江西武宁)双井泉在黄庭坚故居的南边,汲取烹茶,绝对胜过他处的水。
杭州孤山下有金沙泉,唐朝白居易曾经品尝此泉水,甘美可爱。观察其地的沙土,光灿如黄金,所以称作金沙泉。
安陆府沔阳(今湖北天门西北)有陆子泉,又叫做文学泉。唐朝陆羽嗜茶,曾以此泉水试茶,故名。
清代蔡方炳《增订广舆记》记载:玉泉山,泉水从螭石缝间流出,于是把石头凿成螭头,使泉水从螭口中流出,味道极为甘美。聚汇成池,直径达三丈,东边横跨一座小石桥,名叫玉泉垂虹。
《武夷山志》记载:武夷山南虎啸岩有语儿泉,泉水浓得好像停膏,倒入杯中,可以照见毛发,味道甘甜而广大,品尝起来有软绵顺畅的感觉。其次则数天柱山三敲泉,而御茶园的喊泉与此泉不相上下。武夷北山的泉水味道与南山迥然不同。小桃源这个泉,高出地面一尺左右,取之不竭,称作高泉,味道纯美绵远而有逸致,可以说是格调和韵味双全,越品越感到滋味无穷,实在是无法用言语表达。比较差的有接笋的仙掌露,品质最差的,也没有硬冽的气质。
清代徐葆光《中山传信录》记载:琉球烹茶,用茶末掺杂少量细粉放入碗中,倒半瓯沸水,用小竹帚搅动数十次,以瓯中所起的沫饽布满瓯面为度,以此来敬献宾客。另外,还有用大螺壳烹茶的。
清代屈擢升《随见录》记载:安庆府宿松县(今属安徽省)东门外,孚玉山下福昌寺旁边有一口井,叫做龙井,水味清澈甘美,用来烹茶非常好,品质与溪流山泉相比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