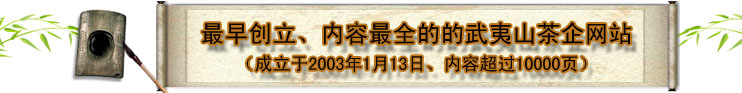|
《吕氏春秋》伊尹说汤五味,“九沸九变,火为之纪”。
许次纾《茶疏》:甘泉旋汲,用之斯良,丙舍在城,夫岂易得。故宜多汲,贮以大瓮,但忌新器,为其火气未退,易于败水,亦易生虫。久用则善,最嫌他用。水性忌木,松杉为甚。木桶贮水,其害滋甚,挚瓶为佳耳。
沸速,则鲜嫩风逸。沸迟,则老熟昏钝。故水入铫,便须急煮。候有松声,即去盖,以息其老钝。蟹眼之后,水有微涛,是为当时。大涛鼎沸,旋至无声,是为过时。过时老汤,决不堪用。
茶注、茶铫、茶瓯,最宜荡涤。饮事甫毕,馀沥残叶,必尽去之。如或少存,夺香败味。每日晨兴,必以沸汤涤过,用极熟麻布向内拭干。以竹编架覆而庋之燥处,烹时取用。
三人以上,止热一炉。如五六人,便当两鼎炉,用一童,汤方调适。若令兼作,恐有参差。
火必以坚木炭为上。然木性未尽,尚有馀烟,烟气入汤,汤必无用。故先烧令红,去其烟焰,兼取性力猛炽,水乃易沸。既红之后,方授水器,乃急扇之。愈速愈妙,毋令手停。停过之汤,宁弃而再烹。
茶不宜近:阴室、厨房、市喧、小儿啼、野性人、僮奴相哄、酷热斋舍。
罗廪《茶解》:茶色白,味甘鲜,香气扑鼻,乃为精品。茶之精者,淡亦白,浓亦白,初泼白,久贮亦白。味甘色白,其香自溢,三者得则俱得也。近来好事者,或虑其色重,一注之水,投茶数片,味固不足,香亦然,终不免水厄之诮,虽然,尤贵择水。
香以兰花为上,蚕豆花次之。
煮茗须甘泉,次梅水,梅雨如膏,万物赖以滋养,其味独甘。梅后便不堪饮。大瓮满贮,投伏龙肝一块以澄之,即灶中心干土也,乘热投之。
李南金谓,当背二涉三之际为合量。此真赏鉴家言。而罗鹤林惧汤老,欲于松风涧水后,移瓶去火,少待沸止而瀹之。此语亦未中。殊不知汤既老矣,虽去火何救哉?
贮水瓮置于阴庭,覆以纱帛,使昼挹天光,夜承星露,则英华不散,灵气常存。假令压以木石,封以纸箬,暴于日中,则内闭其实,外耗其精,水神敝矣,水味败矣。
《考馀事》:今之茶品与《茶经》迥异,而烹制之法,亦与蔡、陆诸人全不同矣。
始如鱼目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涌泉如连珠为二沸,奔涛溅沫为三沸。其法非活火不成。若薪火方交,水釜才炽,急取旋倾,水气未消,谓之嫩。若人过百息,水逾十沸,始取用之,汤已失性,谓之老。老与嫩皆非也。
《夷门广牍》:虎丘石泉,旧居第三,渐品第五。以石泉淳泓,皆雨泽之积,渗窦之潢也。况阖庐墓隧,当时石工多死,僧众上栖,不能无秽浊渗入。虽名陆羽泉,非天然水。道家服食,禁尸气也。
《六研斋笔记》:武林西湖水,取贮大缸,澄淀六七日。有风雨则覆,晴则露之,使受日月星之气。用以烹茶,甘淳有味,不逊慧麓。以其溪谷奔注,涵浸凝,非复一水,取精多而味自足耳。以是知凡有湖陂大浸处,皆可贮以取澄,绝胜浅流。阴井,昏滞腥薄,不堪点试也。
古人好奇,饮中作百花熟水,又作五色饮,及冰蜜、糖药种种各殊。余以为皆不足尚。如值精茗适乏,细松枝,瀹汤漱咽而已。
《竹懒茶衡》:处处茶皆有,然胜处未暇悉品,姑据近道日御者:虎丘气芳而味薄,乍入盎,菁英浮动,鼻端拂拂如兰初析,经喉吻亦快然,然必惠麓水,甘醇足佐其寡薄。龙井味极腆厚,色如淡金,气亦沉寂,而后咀咽之久,鲜腴潮舌,又必借虎跑空寒熨齿之泉发之,然后饮者,领隽永之滋,无昏滞之恨耳。
松雨斋《运泉约》:吾辈竹雪神期,松风齿颊,暂随饮啄人间,终拟逍遥物外。名山未即,尘海何辞?然而搜奇炼句,液沥易枯;涤滞洗蒙,茗泉不废。月团三百,喜拆鱼缄;槐火一篝,惊翻蟹眼。陆季疵之著述,既奉典刑;张又新之编摩,能无鼓吹。昔卫公宦达中书,颇烦递水;杜老潜居夔峡,险叫湿云。今者,环处惠麓,逾二百里而遥;问渡松陵,不三四日而致。登新捐旧,转手妙若辘轳;取便费廉,用力省于桔槔。凡吾清士,咸赴嘉盟。运惠水:每坛偿舟力费银三分,水坛坛价及坛盖自备之计。水至,走报各友,令人自抬。每月上旬敛银,中旬运水。月运一次,以致清新。愿者书号于左,以便登册,并开坛数,如数付银。某月某日付。松雨斋主人谨订。
《茶汇钞》:烹时先以上品泉水涤烹器,务鲜务洁。次以热水涤茶叶,水若太滚,恐一涤味损,当以竹箸夹茶于涤器中,反复洗荡,去尘土、黄叶、老梗既尽,乃以手搦干,置涤器内盖定。少刻开视,色青香冽,急取沸水泼之。夏先贮水人茶,冬先贮茶人水。
茶色贵白,然白亦不难。泉清、瓶洁、叶少、水冽,旋烹旋啜,其色自白,然真味抑郁,徒为目食耳。若取青绿,则天池、松萝及之最下者,虽冬月,色亦如苔衣,何足为妙?若余所收真洞山茶,自谷雨后五日者,以汤荡浣,贮壶良久,其色如玉。至冬则嫩绿,味甘色淡,韵清气醇,亦作婴儿肉香。而芝芬浮荡,则虎丘所无也。
《洞山茶系》:茶德全,策勋惟归洗控。沸汤泼叶即起,洗鬲敛其出液。候汤可下指,即下洗鬲,排荡沙沫。复起,并指控干,闭之茶藏候投。盖他茶欲按时分投,惟既经洗控,神理绵绵,止须上投耳。
《天下名胜志》:宜兴县湖镇,有于潜泉,窦穴阔二尺许,状如井。其源流潜通,味颇甘冽,唐修茶贡,此泉亦递进。
洞庭缥缈峰西北,有水月寺,寺东入小青坞,有泉莹澈甘凉,冬夏不涸。宋李弥大名之曰无碍泉。
安吉州,碧玉泉为冠,清可鉴发,香可瀹茗。
徐献忠《水品》:泉甘者,试称之必厚重,其所由来者远大使然也。江中南零水,自岷江发源数千里,始澄于两石间,其性亦厚重,故甘也。
处士《茶经》,不但择水,其火用炭或劲薪。其炭曾经燔为腥气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古人辨劳薪之味,殆有旨也。
山深厚者,雄大者,气盛丽者,必出佳泉。
张大复《梅花笔谈》: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
《岩栖幽事》:黄山谷赋:“汹汹乎,如涧松之发清吹;浩浩乎,如春空之行白云。”可谓得煎茶三昧。
《剑扫》:煎茶乃韵事,须人品与茶相得。故其法往往传于高流隐逸,有烟霞泉石磊块胸次者。
《涌幢小品》:天下第四泉,在上饶县北茶山寺。唐陆鸿渐寓其地,即山种茶,酌以烹之,品其等为第四。邑人尚书杨麒读书于此,因取以为号。
余在京三年,取汲德胜门外水烹茶,最佳。
大内御用井,亦西山泉脉所灌,真天汉第一品,陆羽所不及载。
俗语“芒种逢壬便立霉”,霉后积水烹茶,甚香冽,可久藏,一交夏至便迥别矣。试之良验。
家居苦泉水难得,自以意取寻常水煮滚,人大磁缸,置庭中避日色。俟夜天色皎洁,开缸受露,凡三夕,其清澈底。积垢二三寸,亟取出,以坛盛之,烹茶与惠泉无异。闻龙《它泉记》:吾乡四陲皆山,泉水在在有之,然皆淡而不甘。独所谓它泉者,其源出自四明,自洞抵埭,不下三数百里。水色蔚蓝。素砂白石,粼粼见底。清寒甘滑,甲于郡中。
《玉堂丛语》:黄谏尝作《京师泉品》,郊原玉泉第一,京城文华殿大庖井第一。后谪广州,评泉以鸡爬井为第一,更名学士泉。
吴云:武夷泉出南山者,皆洁冽味短。北山泉味迥别。盖两山形似而脉不同也。予携茶具共访得三十九处,其最下者亦无硬冽气质。
王新城《陇蜀馀闻》:百花潭有巨石三,水流其中,汲之煎茶,清冽异于他水。
《居易录》:济源县段少司空园,是玉川子煎茶处。中有二泉,或曰玉泉,去盘谷不十里;门外一水曰漭水,出王屋山。按《通志》,玉泉在泷水上,庐仝煎茶于此,今《水经注》不载。
《分甘馀话》:一水,水名也。郦元《水经注·渭水》:“又东会一水,发源吴山。”《地里志》:“吴山,古山也,山下石穴,水溢石空,悬波侧注。”按此即一水之源,在灵应峰下所谓“西镇灵”是也。余丙子祭告西镇,常品茶于此,味与西山玉泉极相似。
《古夫于亭杂录》:唐刘伯刍品水,以中泠为第一,惠山、虎丘次之。陆羽则以康王谷为第一,而次以惠山。古今耳食者,遂以为不易之论。其实二子所见,不过江南数百里内之水,远如峡中虾蟆碚,才一见耳。不知大江以北如吾郡,发地皆泉,其著名者七十有二。以之烹茶,皆不在惠泉之下。宋李文叔格非,郡人也,尝作《济南水记》,与《洛阳名园记》并传。惜《水记》不存,无以正二子之陋耳。谢在杭品平生所见之水,首济南趵突,次以益都孝妇泉[原注:在颜神镇]。青州范公泉,而尚未见章丘之百脉泉,右皆吾郡之水,二子何尝多见。予尝题王秋史[苹]二十四泉草堂云:“翻怜陆鸿渐,跬步限江东。”正此意也。
陆次云《湖杂记》:龙井泉从龙口中泻出。水在池内,其气恬然。若游人注视久之,忽波澜涌起,如欲雨之状。张鹏翮《奉使日记》:葱岭乾涧侧有旧二井,从旁掘地七八尺,得水甘冽,可煮茗。字之曰塞外第一泉。
《广舆记》:永平滦州有扶苏泉,甚甘冽。秦太子扶苏尝憩此。
江宁摄山千佛岭下,石壁上刻隶书六字,曰“白乳泉试茶亭”。
钟山八功德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八蠲疴。
丹阳**泉,唐刘伯刍论此水为天下第四。
宁州双井在黄山谷所居之南,汲以造茶,绝胜他处。
杭州孤山下有金沙泉,唐白居易尝酌此泉,甘美可爱。视其地沙光灿如金,因名。
安陆府沔阳有陆子泉,一名文学泉。唐陆羽嗜茶,得泉以试,故名。
《增订广舆记》:玉泉山,泉出罅石间,因凿石为螭头,泉从口出,味极甘美。为池,广三丈,东跨小石桥,名曰玉泉垂虹。
《武夷山志》:山南虎啸岩语儿泉,浓若停膏,泻杯中,鉴毛发,味甘而博,啜之有软顺意。次则天柱三敲泉,而茶园喊泉可伯仲矣。北山泉味迥别。小桃源一泉,高地尺许,汲不可竭,谓之高泉,纯远而逸,致韵双发,愈啜愈想愈深,不可以味名也。次则接笋之仙掌露,其最下者,亦无硬冽气质。
《中山传信录》:琉球烹茶,以茶末杂细粉少许人碗,沸水半瓯,用小扫帚搅数十次,起沫满瓯面为度,以敬客。且有以大螺壳烹茶者。
《随见录》:安庆府宿松县东门外,孚玉山下福昌寺旁井,曰龙井,水味清甘,瀹茗甚佳,质与溪泉较重。
【译文】
唐朝陆羽《六羡歌》写道:不羡黄金,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唐代张又新《煎茶水记》中说:原刑部侍郎刘伯刍先生,是我尊敬的长辈。他为学精深博大,而且很有鉴识。他曾经比较天下之水与茶叶相适宜的,共分以下七等:扬子江南零水(一作南泠水)第一,无锡惠山寺石水(一作泉水)第二,苏州虎丘寺石水(一作泉水)第三,丹阳县(今属江苏)观音寺井水第四,扬州大明寺井水第五,吴淞江(即苏州河)水第六,淮河水最下品,名列第七。这七种水,我曾经携带茶瓶乘船汲取,亲自品尝比较,的确像刘伯当先生所言。有熟悉浙江水泉情况的朋友提出说我们搜访得不够全面,我曾经记录下来。等到我做永嘉(治今温州)刺史时,经过桐庐江(即钱塘江的桐庐段),到东汉隐士严光垂钓处的严子濑,山溪的水色极为清澈,水味非常寒冷。用来烹煎上好的茶叶,其新鲜馨香的味道不可名状,又超过扬子江南零水很远。等到了永嘉,汲取仙岩瀑布的水来煎茶,也不下于扬子江南零水,因此知道那位朋友的说法的确是可信的。
陆羽谈论适宜煎茶的水,按照顺序有以下二十种: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无锡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蕲州(今湖北蕲春)兰溪石下水第三,峡州(今湖北宜昌)扇子山下虾蟆口水第四,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扬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今江西南昌)西山瀑布泉水第八,唐州桐柏县(今属河南)淮水源第九,庐州(今安徽合肥)龙池山岭水第十,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十一,扬州大明寺水第十二,汉江金州(辖今陕西石泉以东、旬阳以西汉水流域)上游中零水第十三,归州(今湖北秭归)玉虚洞下香溪水第十四,商州(今属陕西)武关西洛水第十五,吴淞江水第十六,浙江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柳州(应为郴州)圆泉水第十八,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原注:用雪水煎茶不可太冷]。
唐代顾况《论茶》中说:以文火细烟煎茶,以小鼎长泉烹煮。
唐代苏《仙芽传》第九卷所载《作汤十六法》(通称《十六汤品》)中说:水,是决定茶之命运的关键。如果名贵好茶而用平常的水来煎,就与一般的茶味道无异了。以煎水的过与不及而言,分三种情况;以注水的缓慢与急迫而言,分三种情况;以茶具来评判,分五种情况;以煎水所用柴薪而言,分五种情况。共计十六种情况,称为十六汤:第一叫做得一汤(指火候适中,语出《老子》:“天得一则清,地得一则宁。”),第二叫做婴汤(指未到火候,刚刚沸腾就断火),第三叫做百寿汤(指火候过头,沸腾多次),第四叫做中汤(指缓急适中),第五叫做断脉汤(指注水不连贯),第六叫做大壮汤(指注水过急过快,水量过头),第七叫做富贵汤(指金银茶具),第八叫做秀碧汤(指玉石茶具),第九叫做压一汤(指瓷器),第十叫做缠口汤(指铜铁锡铅等茶具),第十一叫做减价汤(指陶器),第十二叫做法律汤(指以炭火煎),第十三叫做一面汤(指以火或虚炭煎),第十四叫做宵人汤(指以粪火煎),第十五叫做贱汤(又称贼汤,指以干竹枯叶煎),第十六叫做魔汤(指以浓烟侵夺茶味)。
唐末五代丁用晦《芝田录》记载:唐朝名相李德裕(封卫国公,世称李卫公)喜欢惠山泉,不远千里汲取烹茶。从常州到达京师长安,设置驿马进行传送,当时称作水递。后来有一个和尚说:“我请求为相公打通水脉。”京师有一眼井与惠山泉水脉相通,这样从京师井中汲水煎茶,味道与惠山泉水也没有一点差异。李卫公问他:“井在哪个里巷?”回答说:“就是昊天观常住库的后面。”于是汲取惠山泉水、昊天观井水各一瓶,同时夹杂其他泉水八瓶,让和尚辨别清楚。和尚只取了惠山泉水、昊天井泉,李德裕大为惊叹。
南宋祝穆《事文类聚》记载:唐代李德裕(赞皇人,故称赞皇公)在朝当政的时候,有亲信的人奉命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公干。李德裕对他说:“回来的时候,将金山下扬子江南零水取一壶回来。”其人恭敬应诺。等到办完事务乘船回来的那天,因为醉酒而忘记了,乘船到南京石头城下才想起来,乃从长江中汲取一瓶水,回到京师献上。李德裕品饮之后,非常惊讶,说道:“扬子江水的味道与以往不同了,此水很像是南京石头城下的水。”其人当即承认错误,不敢有所隐瞒。
《河南通志》记载:卢仝茶泉在济源县。仝有庄,在济源县的通济桥二里多的地方,茶泉就保存在那里。卢仝有诗写道:“买得一片田,济源花洞前。”他自号玉川子,有寺名玉泉。汲取此寺的泉水,可以用来煎茶。卢仝还有《玉川子饮茶歌》,其中多有奇词警句。
《黄州志》记载:陆羽泉在薪水县(今湖北浠水县)凤栖山下,也叫做兰溪泉,陆羽品评为天下第三泉。曾经汲取此泉水烹茶,宋朝王禹(字元之)有《陆羽泉茶》诗。
无尽法师《天台志》记载:陆羽品评天下泉水,以天台山瀑布泉水为天下第十七水。我曾经试验品饮,比余豳溪、蒙泉的水品质差得多。我因此怀疑陆羽仅仅到过瀑布泉罢了。如果他遍历天台山各处泉水,当不会取金山下扬子江南零水为天下第一了。
宋代叶廷硅(字嗣忠,崇安人)《海录碎事》中说:陆羽品水,以雪水为第二十,因为用雪水煎茶过慢而且太冷。
明代陆树声(字与吉,号平泉,华亭人)《茶寮记》记载:唐朝秘书省中的泉水最好,所以称作秘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