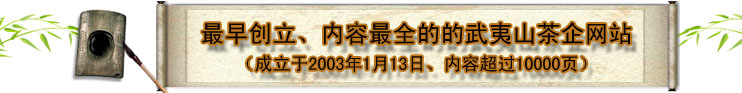|
《檀几丛书》记载:唐朝天宝(742-756)年间,有一位稠锡禅师,名叫清晏,云游卓锡南岳衡山涧上,泉水忽然迸发出来,石窟间有字叫真珠泉。禅师品饮之后,感觉清凉甘甜,十分可口,于是说道:“用此泉水冲泡我家乡的桐庐茶,不是很相称吗?”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说:品评水的高下,以清澈、量轻、甘甜、洁净为美。而煎茶的时候火候的把握,则以水刚烧开沸腾起泡如鱼目、蟹眼般接连不断地迸发跳跃的程度为最好。
《咸淳临安志》记载:栖霞洞内有一个水洞,深不可测,其中的泉水极为甘甜清凉。苏颂(赠魏国公,世称苏魏公)曾经用此水煎茶。另外,莲花院中有三口井,其中露井水质最好,汲取用来烹茶,清甜寒冽,被品评为小林第一。
北宋王钦臣《王氏谈录》中说:先生说名茶品质高而且年代久的,贮藏时间一定稍微长些。遇到出产茶叶的地方,初春采摘新芽轻轻烘焙,与陈茶掺杂一起烹点,香味自然还存在。米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海岳外史)以此进行试验,效果甚好,曾经告诉蔡襄(字君谟),蔡襄也认为是这样。
宋代欧阳修《浮槎山水记》记载:浮槎山与龙池山都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境内,但比较两地泉水的味道,龙池水远远比不上浮槎水。而唐代张又新《煎茶水记》以龙池水为第十,而浮槎水则摈弃而不加记载,因此可知张又新的缺漏很多。陆羽则不是这样,他论水说:“山水上,江次之,井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语虽然简略,而对于品评水来说已经穷尽了。
宋代蔡襄《茶录》中说:有时茶饼贮存达一年以上,其香气、色泽、味道都已陈旧了。煎茶的时候首先要把茶饼放在干净的器皿中用开水浸泡,刮去表面的膏油,刮掉一两层即可停止,然后用茶钤夹住茶饼,文火烤干,然后碾碎成末,烹煮饮用。如果是当年的新茶,就不必用这种方法了。
碾茶的时候,首先要用干净的纸把茶饼紧密地封裹起来捶碎,然后再把碎茶放进茶碾,反复压碾。碾出的茶末大体上是刚刚碾出时色泽鲜白,如果过了一夜,色泽就变得昏暗了。
碾出的碎茶要用茶罗筛成细末。如果茶罗过细,烹煮时茶末就会浮于水面;如果茶罗过粗,烹煮时水沫则会浮在茶上。
候汤(即观察开水的变化,把握恰当的时机投入茶末进行烹煮)是饮茶中最难把握的一个环节。水温没有达到火候,投入茶末后水沫就会漂浮在水面;如果超过了火候,投入的茶末就会沉底。前人所谓的蟹眼,就是指超过了火候的开水。况且水是放在茶瓶中煮的,水温的变化不易分辨,所以说候汤是最难的。
点茶的时候,茶与水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茶少水多,就会使云脚涣散;如果水少茶多,就会使粥面凝聚。[原注:建安人称点茶之后茶汤表面的幻象叫做云脚、粥面。]用茶匙取茶末一钱放入茶盏,先注入开水调和得很均匀,再注入开水,同时用茶筅旋转搅动茶汤。茶盏中注水达到四分就停止,观察茶汤的表面颜色鲜白,着盏之处没有水痕的为最好。建安人斗茶时,以先出现水痕的为负,保持很久没有水痕的为胜。所以他们比较胜负的说法,叫做相去一水两水。
茶叶有其天然的香气,而进奉朝廷的贡茶往往用少量的龙脑和入茶膏,想以此增加茶的香气。建安民间斗茶品茗,都不添加香料,唯恐侵夺了茶叶本身的天然香气。如果在烹煮点茶之际,又掺杂进去一些珍贵的果品、香草,那么其侵夺茶叶的天然香气就会更加严重,的确不应当使用。
宋初陶谷《清异录》中说:注汤点茶的时候,能够在汤面上幻化出各种物象,这是茶艺高手可以通神的技艺。福全和尚生于金乡(今属山东),成长在盛产茶叶的地方,能够在注汤的时候在茶汤表面变幻出图案和文字,形成一句诗,连续点茶四瓯,合成一首绝句,浮于茶瓯的表面。小小的物类,唾手可以办成。施主每天登门布施,要求观看汤戏。福全和尚自己创作了一首吟咏汤戏的诗:“生成盏里水丹青,巧画工夫学不成。却笑当时陆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茶事从唐朝开始兴盛。近代以来有在点汤击拂的时候运用茶匙,另外使用妙法,使茶汤表面的茶纹水脉幻化出各种物象的,例如禽兽、虫鱼、花草之类,纤巧如同绘画。只是可能瞬间就会消散。这就是饮茶的变化,当时的人们就称作“茶百戏”。
还有一种叫做漏影春法的煮茶方法,是用剪好的纸贴到茶盏的里面,投入茶末之后就去掉纸,假装成花身;另外用荔枝的果肉作为叶子,松子、银杏之类的珍贵果品作为花蕊,然后加入开水,点汤击拂。
宋代叶清臣《述煮茶泉品》中说:我年轻的时候看到温庭筠的《茶说》(即《采茶录》),曾经记得他所谈到的泉水的名目大约有二十个。后来适逢向西游历到达巴峡,经过虾蟆窟(即虾蟆口水,张又新品为天下第四水);向北游历小憩芜城(今扬州西北),汲取蜀冈井水(当即扬州大明寺水);向东游历金陵故都,渡过扬子江,在丹阳(今江苏镇江)逗留时酌取丹阳观音寺泉水;经过无锡时,汲取惠山寺泉水。将茶叶碾成细末,以兰桂等作为燃料,用鼎或者缶作为茶器,烹点品饮,无不感到清心涤虑、除病解酒,祛除卑鄙吝啬的机心,招致神明达观的精神。的确可以说是物类的相得益彰,气味的感应而发,这些都是幽人隐士的高雅习尚,是前贤往圣的精审品鉴,实在是不可企及。
从前郦道元精于《水经》,可是却不曾通晓茶事。王肃有饮茶的癖好,可是却不见他谈论水品。至于能同时表彰茶、水这两件美事,我差不多可以感到无愧。
宋代魏泰(字道辅,号溪上丈人,襄阳人)《东轩笔录》记载:鼎州(治今湖南常德)以北百里,有甘泉寺,在大道的左边,其泉水清澈甘美,最适宜煎茶。这里山林环抱,环境幽胜。名相寇准(字平仲,封莱国公,世称寇莱公)被贬官雷州(治今广东海康)时经过这里,酌取泉水,题壁而去。不久,丁谓(字谓之,封晋国公,世称丁晋公)被流放朱崖(治今海南琼山东南),又从这里经过,拜祭佛像并留题而行。天圣(1023-1032)年间,范讽(字补之)以殿中丞出任湖南安抚使,来甘泉寺中看到两位丞相的题诗,徘徊良久,感慨万分,作诗题于其旁边道:“平仲酌泉方顿辔,谓之礼佛继南行。层峦下瞰岚烟路,转使高僧薄宠荣。”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宋哲宗元六年(1091)七夕的这一天,苏东坡当时正担任扬州知州,与发运使晁端彦(字美叔)、苏州同知晁补之(字无咎)在大明寺汲取塔院西廊井与下院蜀井两种水,比较其高下,结果以塔院西廊井水为佳。
华亭县有寒穴泉,与无锡惠山泉水味道相同,同时品尝,感觉不到二者的差异,当地人也很少知道。王安石(字介甫,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曾有诗吟咏道:“神震冽冰霜,高穴雪与平。空山淳千秋,不出呜咽声。山风吹更寒,山月相与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烦酲。”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我同年考中进士的朋友李南金说:陆羽《茶经》分别以鱼目、涌泉、连珠三个词来形容煮水三个阶段的标志。可是近世以来煎茶煮水很少用鼎,而改用茶瓶来煮水,难以观察把握。这就应当以煮水的声音来分辨一沸、二沸、三沸。另外,陆羽的煮水方法,因为没有就茶投茶烹点,所以以第二沸作为下茶的最佳时机。如果按照如今的煎茶方法,以沸水就茶瓯中冲点,则应当以背二涉三之际也就是二沸已过刚到三沸之时作为停火点茶最佳时机。于是写下一首专咏声辨的诗:“砌虫唧唧万蝉催,忽有千车捆载来。听得松风并涧水,急呼缥色绿磁杯。”其论述已经非常精到了。
然而,瀹茶的方法,煮水要嫩,而不可过老。因为水嫩就会使茶味甘香,水老就会使茶味过苦。如果煮水时声音像松风声起、涧水流淌的时候,急忙进行烹点,难道不是过于水老而味苦吗?只有赶忙移开茶瓶,稍微等待其沸腾平息而进行烹点,然后会使煮水老嫩适中而茶味甘香。这是李南金所不曾探究的。于是我补充了一首诗:“松风桂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南宋赵彦卫(字景安,宋宗室)《云麓漫钞》中说:陆羽鉴别天下的水味,各立名品,各地都有石刻行于当世。《列子》上说:孔子说过:“淄渑之合,易牙能辨之。”易牙是齐威公(即齐桓公)的大夫,淄渑二水(在今山东省,二水滋味不同,合在一起则不易辨)的滋味,只有易牙能够分辨出来。齐威公不相信,数次试验都很灵验。陆羽难道也是得到了易牙的遗意吗?
北宋黄庭坚《黄山谷集》记载:泸州(今属四川)大云寺西偏悬崖石头之上,有泉水滴沥,一州所有的泉水都比不上这里。
北宋林逋(字君复,钱塘人,谥和靖先生)《烹北苑茶有怀》诗写道:石碾轻飞瑟瑟尘,乳花烹出建溪春。人间绝品应难识,闲对《茶经》忆古人。
苏轼《东坡集》中说:我近来从京师开封经汴水入淮河,进而泛长江西去,通过三峡逆流而上回到故乡四川,一路之上饮用江淮之水整整一年有馀。回到故乡之后,感觉到井水腥涩,直到百馀天后才适应下来。由此可知,江水要比井水甘甜,千真万确。如今来到岭南,从扬子江开始饮用江水,等到了南康(今江西赣州),水流更加清澈,江水也更加甘甜,由此知道南方的江水又比北方的江水更好。近来又翻过五岭到达清远峡(在今广东清远市),水色犹如碧玉,水味更好。今天游历罗浮山,酌取泰禅师的锡杖泉水,就感到清远峡水又在其下了。岭南地区只有惠州人喜欢斗茶,可见此水没白流啊!
无锡惠山寺,东边有观泉亭,上有匾额“漪澜”,泉水就在亭中,两个井石(即井壁)相距咫尺,却一方一圆形态各异。汲取泉水的人们多从圆井汲水,因为方者易动而圆者易静,静者清澈而动者浑浊。泉水流过漪澜亭,从石龙口中流出,汇入下面的大池之中后,就有了土气,不可汲取饮用。惠山泉水一年四季不会干涸,张又新品评为天下第二泉。南宋叶梦得(字少蕴,号石林)《避暑录话》中说:唐代名臣裴度(字中立,封晋国公,世称裴晋公)有诗写道:“饱食缓行初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他写下这首诗必定自以为很得意,然而我在山中居住了七年,享受此等生活多了。
金代冯璧(字叔献,别字天粹,真定人)《东坡海南烹茶图》诗写道:讲筵分赐密云龙,春梦分明觉亦空。地恶九钻黎火洞,天游两腋玉川风。
《锦绣万花谷》中说:黄庭坚有《井水帖》写道:“取井旁边小石头十数个,放入瓶中,可以使瓶中的水不浑浊变质。”所以他《咏惠山泉》诗中有“锡谷寒泉椭石俱”的句子。石头圆而且长,就叫做椭,是用来澄清水质的。
制茶人家碾茶,须要碾茶碾到眉毛皆白的程度,乃可称得上最好。曾几(字吉甫,号茶山居士)有诗写道:“碾处须看眉上白,分时为见眼中青。”南宋祝穆《舆地纪胜》记载:竹泉,在荆州府松滋县(今属湖北)南部。北宋至和(1054-1056)初年,苦竹寺的和尚淘井以疏通水源,淘得一支毛笔。后来黄庭坚贬官贵州从此经过,仔细审视毛笔说:“这是我在虾蟆碚所坠落水中的那支笔。”由此可知竹泉与虾蟆泉是相通的。黄庭坚有诗写道:“松滋县西竹林寺,苦竹林中甘井泉。巴人谩说虾蟆碚,试裹春茶来就煎。”北宋周辉《清波杂志》记载:我的故乡无锡惠山,其泉水、美石都是士大夫几案间的玩赏之物。每有亲朋故旧东来,多次通问松竹平安讯息,而且经常带来陆子泉水(即惠山泉,宋代在惠山建陆子泉亭,故称)使我得以不时品饮,茗碗不致落寞。但是往岁也有人送惠山泉水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不免会带有久贮瓶盎的气味。如果用细砂淋滤一过,就会像刚刚汲取一样新鲜,称作拆洗惠山泉。浙江天台山的竹沥水,当地人砍断竹稍,使竹身弯曲过来汲取其中的竹沥水满瓮,如果掺杂其他的水,就会马上败坏水味。苏舜元(字才翁)与蔡襄(字君谟)斗茶,蔡襄所用的茶叶很好,而且以惠山泉来煎煮;苏舜元的茶叶较差,但用竹沥水来煎煮,就能够取胜。这种说法见于江休复(字邻几)所著的《嘉杂志》。
果真如此,那么如今喜欢点汤击拂斗茶的人们,为什么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件事呢?江西的双井茶和双井泉,因为黄庭坚(号山谷道人)的缘故才为世人所重。苏颂(赠魏国公,世称苏魏公)曾说过,平生举荐的人才不知有多少,只有孟安序朝奉每年以一瓮双井泉水赠送给我。因为苏魏公不接受馈送礼物,但是却单单接受双井泉水,也可说明双井泉水是如何受珍重啊!
北宋宋敏求《东京记》记载:文德殿的两侧,有东西上门。所以杜诗写道:“东上阁之东,有井泉绝佳。”黄庭坚《忆东坡烹茶》诗写道:“门井不落第二,竟陵谷帘空误书。”北宋陈舜俞《庐山记》记载:庐山康王谷有瀑布,飞泉破岩而下的有二三十个支派,宽度达七十多尺,其高则不可胜计。黄庭坚诗中所吟咏的“谷帘煮甘露”,就是指的庐山康王谷的飞泉。
孙月峰《坡仙食饮录》记载:唐朝人煎茶多用姜作为辅料,所以唐代诗人薛能(字太拙,汾州人)有《蜀州郑史君寄乌觜茶因以赠答八韵》诗写道:“盐损添常戒,姜宜著更夸。”由此可知,还有用盐作为作料的。近代以来如果有此二物作为作料煎茶,人们就会大笑之。然而,中等的茶叶用姜作为作料煎煮的确不错,但用盐煎则不可以。
明代冯可宾《茶笺》中说:罗茶虽然同样出产于山,但不同地方所产依然多有差别。如果茶叶有兰花香味,味道甘美,经过霉天(农历入伏前的几天,潮湿发霉,故称)和秋天,打开茶坛烹煮,其香味更加浓烈,味道就像刚刚冲泡的一样,汤色鲜白,就是真正的洞山所产的茶。其他地方所出的茶叶刚刚采制时也很香,经过秋天就索然无味了。
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说:世人的情性嗜好各不一样,可是喜欢饮茶却达到十分之九。以竹炉煮茶,把盏清谈,烹煮引来清风的碧云(即茶叶),倾注浮花满瓯的雪乳(即茶汤),如果不借助于泉水的功勋,如何能够昭显茶叶的品德?概略而言,其方法有五个关键:一是选择泉水,二是选择茶具,三是忌讳污秽不洁,四是谨慎烹煮,五是分辨汤色。
明代徐献忠(字伯臣,号长谷,华亭人)《吴兴掌故录》(一作《吴兴掌故集》)记载:湖州金沙泉,元代至元(前至元为1264-1294,后至元为1335-1340,查《吴兴掌故集》原文为至元十五年,显然是前至元)年间中书省派遣官员前去祭祀。一夕之间泉水外溢,可以灌溉田地千亩,赐名为瑞应泉。
《职方志》记载:广陵(今江苏扬州)蜀冈上有一口井,名叫蜀井,是说其泉水与西蜀相通。茶圣陆羽品评天下泉水,共有二十种,蜀冈水名列第七(当为第十二大明寺水)。
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说:大凡点茶,首先必须将茶盏烘烤令热,这样就会使茶面汤花凝聚,如果茶盏冷的话就会使茶色不能散发出来。
明代陈继儒《太平清话》中说:我曾经酌取中泠泉水(在今镇江金山)烹茶,味道比惠山泉水要差,感到实在不可理解。后来经过考证,才知道陆羽原本以庐山康王谷帘泉为第一。《山疏》上说:“陆羽《茶经》曾经说过,瀑泻湍急的水不可饮用。如今这庐山瀑布,可以说瀑泻湍急无水可比,却认为天下第一,这是为什么呢?又有一个云液泉在谷帘水的旁边,山中多出云母,云液泉乃是云母的汁液,泉水只有如指头大的水流,清凉甘美,远远超出谷帘水之上,却不能得到第一,这又是为什么呢?”还有碧淋池东西两泉,水味都极为甘甜馨香,不比惠山泉水差,其中的东泉尤其甘测。
蔡襄认为煮水取其鲜嫩而不取过老,这是针对团饼茶而言的。如今茶叶不经过碾罗加工,都是自然的芽叶枝梗,如果水热不够就不能使茶的精神发越、色泽显现,所以斗茶的取胜法宝,尤其在于煮水到五次沸腾之时进行冲泡。
明代徐渭《煎茶七类》中说:煮茶不是一件随意作为的事情,关键是必须要求人的品质与茶的品性相得益彰,因此煎茶之法往往流传于高人隐士,有烟霞泉石堆积胸中也就是向往山林隐逸生活的人。
品评泉水,以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为下。如果不得已而用井水,则要取经常汲取的,汲取得多水性就活。
烹茶要用活火,观察水泡鳞鳞泛起,到达沸腾,就把茶叶放到茶具中,先倒入少量开水,等到茶与水相溶,再倒满开水,这时水汽渐开,沫饽浮于茶面,茶味就会散发开来,达到最佳效果。因为古时茶叶用团饼碾成碎末,味道容易散发出来,叶茶冲泡太急就不易出味,过于煮熟则味道浑浊不清而沉积不通。
明代张源《茶录》中说:山顶的泉水清澈而较轻,山下的泉水清澈而较重,石中流出的泉水清澈而甘甜,沙中渗出的泉水清澈而寒冽,土中形成的泉水清澈而绵厚。流动的泉水要比静止不动的泉水好,在山的北面背阴的泉水要比在山的南面向阳的泉水好。山势陡峭的地方泉水就少,山势挺拔俊秀的地方就有神韵。真正的天然泉源的水是无味的,真正的天然泉水是没有香气的。从黄色的石头中流出的泉水比较好,从青色的石头中流出的泉水则不能饮用。
关于烹茶煮水火候的把握,有三大辨别标准:第一叫做形辨,第二叫做声辨,第三叫做气辨。形辨就是通过水性加以鉴别,称为内辨;声辨就是通过水声加以鉴别,称为外辨;气辨就是通过水汽加以鉴别,称为捷辨。其中形辨又可以分为四小辨:水面浮起水泡如虾眼、如蟹眼、如鱼眼、连珠,这四种都是萌汤也就是刚刚烧热的水,直到水面汹涌沸腾如腾波鼓浪,水汽全部消散,才达到了纯熟。声辨又可以分为五小辨:如初起之声、旋转之声、振动之声、骤雨之声,这四种声音都是萌汤,直到无声,才达到了纯熟。气辨又可以分为六小辨:如水汽漂浮起一缕、二缕、三缕,以及漂浮的气缕混乱不分、水汽氤氲环绕飘动,这五种水汽都是萌汤的标志,直到水汽升腾冲贯,才达到了纯熟。
蔡襄认为茶汤用嫩而不用老,这是因为古人制茶必须经过碾、磨、罗等工序,制成茶饼,这样茶末见水之后,其神韵便会很快散发出来,这就是茶汤用嫩而不用老的原因。如今制茶,不再使用茶罗、茶碾进行加工,而是完全保持茶叶天然形色的芽叶状态,这样茶汤就必须达到纯熟,才能使茶叶的神韵得到充分发挥。
烹茶的时候,炉火要烧得通红,才把茶铫放在炉火之上。用扇子扇火,开始时要又轻又快,等到水热发出声音时稍微用力又重又快,这就是所谓的文武之火候。火力过于文,那么烧出来的水性就柔和,水性柔和就会为茶所降伏;火力过于武,那么烧出来的水性就猛烈,水性猛烈茶就会为水所制导。这两种情况都不足以称得上中正平和,不符合茶人和鉴赏家的茶艺要旨。
往茶壶中投放茶叶要有一定的程序,不能违背其适宜的标准。先放茶叶后冲开水,叫做下投;先冲半壶开水再投放茶叶,然后注满开水,叫做中投;先注满开水后投放茶叶,叫做上投。这三种方法要根据季节的变化而分别运用,夏季适宜上投,冬季适宜下投,春秋两季则适宜中投。
茶事活动不适宜使用的人和物包括:贱劣的树木、破败的器具、铜勺、铜铫、木桶、木柴、烟煤炭、笨手笨脚的童子、相貌丑陋的女佣、不洁净的手巾、各种各样的果实香药等。(此则不见于《茶录》而见于《茶疏》)明代谢肇《五杂俎》记载:唐代薛能《茶诗》(即《蜀州郑史君寄乌觜茶因以赠答八韵》)写道:“盐损添常戒,姜宜著更夸。”这样来煮茶,茶味怎么会好呢?此事或许是发生在陆羽品题之前。到了苏东坡《和蒋夔寄茶》诗中写道:“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可见已经知道这种做法不正确,可是这种习俗依然存在。如今的江西和湖广地区的人们,还有以姜煎茶的。虽然说是古风犹存,终究感到不合典则。
福建人苦于山泉难以得到,多用雨水煎茶。其甘甜的味道虽然比不上山泉,但清洌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淮河以北地区,雨水味苦色黑,无法用来煮水烹茶。只有雪水可用,冬天收藏雪水,入夏用来煮水烹茶,效果非常好。雪本来是雨水所凝结而成的,煮水烹茶适宜雪水却不宜雨水,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北方的瓦屋不洁净,多用污泥涂抹填塞而成,故而雨水也不洁净。
古时候泡茶,有称煮茶,有称烹茶,有称煎茶,必须等到水面起泡如蟹眼连珠,茶味方为适中。如今的茶叶,只要以沸水冲泡,稍微着火,就会色泽泛黄、味道涩苦而不能饮用了。由此可知,古今的煮茶方法,自有其不同。
宋代苏舜元(字才翁)与蔡襄斗茶,用天台山的竹沥水,应当是竹露水而不是竹沥水。如果像今天医生用火逼竹取沥的方法,所取的竹沥水绝不适合用来煎茶。
明代顾元庆《茶谱》所说的煎茶四要:第一是择水,第二是洗茶,第三是候汤,第四是择品。点茶三要:第一是涤器,第二是盏,第三择果。
明代熊明遇《山茶记》(一作《罗茶记》)中说:烹茶,水的功用至关重要。没有山泉就使用雨水,秋雨最好,梅雨次之。秋雨甘洌而色白,梅雨醇厚而色白。雪水是五谷的精华,色泽不能过白。保养雨水要放置石子于盛水的瓮中,不仅能增益水质,而且白石清泉,悦人心目,会心处并不在远。
乐纯《雪庵清史》中说:我生性喜欢清苦,恰好与茶的本性相适宜。所幸的是我的家乡邻近茶叶产地,可以随意品饮尽兴。只是当地友人不了解三火、三沸的烹茶方法,我每次过往品茶,不是烹点过老,就是太嫩,以至于让茶叶的甘香的美味荡然无存,其原因大概是误听了李南金的说法。只有像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论,才称得上是把握住了煎茶的火候。友人说:“我生性只喜欢读书,游玩好山水,参禅拜佛,或者经常饮酒醉倒花前,不喜欢品茶,因此对把握煎茶的火候不精通。古人曾经说过,饮茶对于消除郁闷积滞,短期的利益暂时很好;耗费元气精神,终身之危害却很大。获取好处就归功于茶叶,贻害身体却不说茶叶的灾害。甘心承受世俗的名声,就是这样的缘故。”唉!茶叶的冤枉太大了。怎么不听听秃翁的说法:消除郁闷积滞,坚持清苦生活的好处的确很多;耗费元气精神,放纵情欲的危害最大。得到了好处却不说是饮茶的功劳,自我放纵的危害反而归咎于饮茶。况且把握不好火候,不仅仅对饮茶而言。读书而不能够获得其中的趣味,游历山水而不能够陶冶自己的性情,参禅拜佛而不能够参破其根本,喜欢饮酒赏花而不能够获得其中的韵致,都是没有把握火候的表现。难道仅仅是因为我喜欢品茶而故意为茶说好话吗?也就是想以此清苦之味,与故人共享共勉罢了。
煮茶的方法有六个关键:第一是辨别茶叶,第二是选择泉水,第三是把握火候,第四是煮水,第五是选择茶具,第六是品饮。茶叶的分类有粗茶,有散茶,有末茶,有饼茶。相对应的制作方法有斫(将粗茶切碎煮饮)、熬(散茶蒸青后直接烘焙,然后煮饮)、场(末茶烘焙碾研成末以后煮饮)、舂(饼茶的制作工艺和品饮方法)。我有幸懂得了加工茶的方法,同时也掌握了烹茶的六个关键,每当遇到亲朋好友,便亲自煎茶烹饮。但愿通过一瓯佳茶能够经常得到自然真性,而不用搜肠刮肚的文字五千卷。因此说品饮的现实意义的确很深远啊!
明代田艺蘅《煮泉小品》中说:茶是我国南方的一种优良的常绿树种,是人们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饮料。其品质固然有善恶好坏的分别,但是若得不到好的泉水,而且烹煮不得其法,即使是好茶也达不到上佳的效果。只要饮泉而感觉精神清爽,品茶而忘掉尘世喧闹,这都不是膏梁子弟、纨绔之人所可谈论的。于是编撰《煮泉小品》,与那些幽人隐士进行商榷。(此节见赵观《叙》)陆羽曾经说过:“就在产茶之地汲水烹茶,没有效果不佳的,这是因为水土相适宜。”这种说法的确是精妙之论。况且随即采摘随即烹煮,茶叶和泉水二者都非常新鲜呢!因此五代毛文锡《茶谱》也说“四川蒙山中顶上清峰的好茶,如果能获取一两,用本地的泉水烹煮服用,就能祛除长期的病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杭州各处的泉水,只有龙泓能够列入佳品,而当地的茶叶,也只有龙泓山出产的最好。因为此山深厚高大,清秀壮丽,是南北两山的主峰。所以其泉水清澈寒冷、甘测芳香,非常适宜煮茶。元代文学家虞集(字伯生,号道园)有诗写道:“但见瓢中清,翠影落群岫。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明代姚绶(字公绶)诗写道:“品尝顾渚风斯下,零落《茶经》奈而何!”其独特风味从中可以想见,又何况这里曾经是葛仙翁炼丹的所在呢!在龙泓的上面还有老龙泓,其寒冷清澈又两倍于龙泓。其地出产茶叶为南北两山的绝品。茶圣陆羽品第钱塘天竺、灵隐二寺的茶叶为下品,当是尚未认识此茶。而当地方志中也只记载有宝云、香林、白云等茶,都比不上龙泓茶的清香馥郁、滋味绵长。
我曾经对上述各种茶叶一一进行品尝,得出的结论是龙井茶叶和泉水堪称双绝,两浙地区没有能与之相比的。
山体厚重,那么其中的泉水味道就醇厚;山势奇特,那么其中泉水的味道就奇异;山脉清秀,那么其中泉水的味道就清澈;山峦幽深,那么其中泉水的味道就幽静。这都是泉水中的佳品。如果不醇厚,就会淡薄;不奇异,就会笨拙;不清澈,就会浑浊;不幽静,就会喧嚣,也就一定不会发挥其作用。
江,就是公共的意思,是说众多的河水都汇流其中。许多河水汇流一起,味道就会混杂,所以陆羽《茶经》中说“江水次之”。他还说“饮用江水要汲取离开人们生活区域较远的”,这是因为离开人们生活区域较远的地方,水会比较澄清,而且不会因为荡漾而味道浇漓。
浙江桐庐的严子濑,也叫七里滩,因为在砂石上叫做濑、叫做滩,总称为浙江,但是潮汐不如钱塘江,而且水深而清澈,所以列入了陆羽的泉品。我曾经在清秋时节乘船停泊于严子陵钓台之下,取出行囊中的武夷、金华两种茶,进行烹试。本来是同一种水,可是烹出的茶却有很大差别:武夷茶则显得色黄而燥冽,金华茶则显得碧绿而清香。于是可知在选择水的同时,还要选择茶。陆羽以婺州茶为次,而叶清臣以北苑贡茶的白乳比武夷茶为好,可是如今则其茶的优劣正好相反。通晓其意的行家认为这就是所谓的离开了茶的原产地进行试验的缘故,其中泉水的功效占有一半。
如果泉水相去更远一些,不能亲自去汲取,必须派遣诚实的山间童子去汲取,以免出现石头城下假冒名泉的故事。
宋朝诗人苏轼(字子瞻)喜欢玉女河水,吩咐僧人调取水符去汲取,也曾叹惜得不到枕流的佳泉。所以宋朝诗人曾几(号茶山)在《吴傅朋送惠山泉两瓶并所书石刻》诗中有“旧时水递费经营”的句子。
如果茶汤煎得沸点不够,就不能使茶的自然真味充分发挥出来;如果超过了沸点,水煮得过老则会使茶力消乏,失去清香。只有达到有花而无衣即烹点时泛出汤花而没有水痕的境界,才算是掌握了烹点冲瀹的火候。
有了好水,有了佳茶,还不可无火。并不是说真的无火,而是火候没有把握好。唐人李约说:“茶必须用缓火即文火烘烤,用活火进行煎煮。”活火是指有火焰的炭火。苏东坡《汲江煎茶》诗中所说的“活水仍将活火烹”,就是这个意思。我则认为山居之中不可能常常有炭,况且炭是已经燃烧过的死火,不如用于枯的松枝前茶为妙。如果在秋冬季节多捡些松果,储备作为煎茶的燃料,就更为风雅。
人们一般只知道煎水的征候,而不懂得把握烧火的征候。火燃烧起来就会使水蒸发,因此试验火力要比试验水温更为重要。《吕氏春秋·本味篇》上说:伊尹以调和五味之说向商汤进言,其中说到五味三材、九沸九变,而以火候作为其鉴别的标准。
明代许次纾《茶疏》中说:甘洌的泉水刚刚汲取来时,就用来煎茶品饮效果非常好。然而寒舍在城市,怎么能够轻易得到新鲜的泉水呢?因此应当一次多汲取些,贮存在大瓮之中。但最忌讳用新的水容器,因为烧制的火气尚未消尽,容易败坏水味,而且容易生虫。长期使用的容器最好,但最忌讳兼作他用。水的本性很忌讳木器,尤其是松木和杉木更不行。以木桶贮存泉水,其危害非常严重,还不如拿瓶子装水为好。
在煮水的时候,如果水烧开得迅速,那么味道就鲜嫩可口,清馨宜人;如果开水烧得迟缓,那么味道就会因为茶叶过熟而混沌不纯,兼有熟汤之气。所以泉水一放入茶铫,就必须急忙进行烹煮。等听到有松涛声起,就马上揭开盖子,以便观察和把握水的老嫩程度。水面冒出蟹眼似的水泡后,就开始有了微微的波涛,这就正当水烧开的火候。等到水面波涛汹涌,水声鼎沸,一会儿就又无声无息了,这就已经超过了火候。超过了火候就使得开水过老而香气失散,决不可以再用来烹茶了。
茶注、茶铫、茶瓯等器具,最应该保持干燥洁净。每次品饮刚刚结束,就一定要把剩馀的茶水残叶清除干净。如果有一些残留,就会侵夺茶的香气、败坏茶的味道。每天早晨起来,一定要用开水烫好洗净,用极熟的黄麻做成的巾帕把里边擦拭干净,用竹编的架子,把这些茶具扣在上面,放置到干燥的地方,烹茶时再随手取来使用。

|